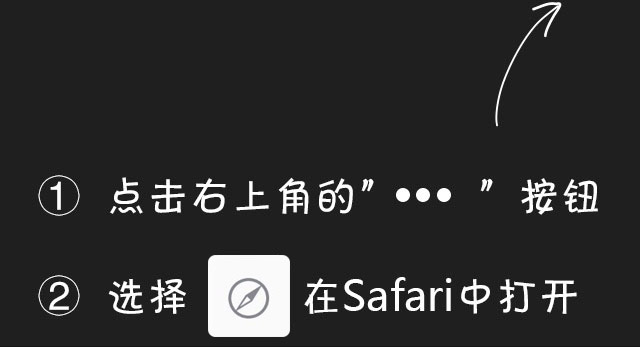如果在看完街对面的(慕尼黑巴伐利亚)老绘画陈列馆之后,你觉得作品过于久远且宗教味儿十足略显沉重的话,那么当你迈进新绘画陈列馆之后,光凭建筑设计你就会觉得走近了现代。
尽管建造时间接近,但新绘画陈列馆在二战期间不幸遭到破坏,德国人于1949年将旧址彻底拆除并重新兴建了如今颇具现代感的新馆。1981年新馆正式对公共开放,设计师为这座后现代主义建筑留有充足的自然光线,既节约能源,又能通过光线的变化体现建筑的空间感和立体感。德国人严谨且务实的设计风格绝非浪得虚名。与建筑设计相得益彰的则是馆藏的19世纪大量清新唯美的风景及肖像画,这其中尤以馆内庞大的印象派绘画收藏值得大书特书。
也就一个世纪多前,印象派绘画在挑战世人审美的同时也遭受着猛烈的质疑与抨击。而100多年后的今天,印象派收藏的数量与品质已经或多或少成为衡量一家欧洲大博物馆的“无形标准”,充分证明了经典艺术绝对是经得起历史的沉淀的。应该说,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陈列馆新馆的印象派收藏在我游历的欧洲各大博物馆中都应属前列。
现存六幅的梵高《向日葵》真迹这里就有一幅,莫奈的《睡莲》,马奈的《莫奈在他的工作船上作画》,塞尚的《自画像》,雷诺阿的《从蒙马特公园远眺建造中的圣心教堂》,梵高的《奥维尔的田地》等等名作更是悉数在列。
三年前在柏林博物馆岛上的老国家画廊和慕尼黑巴伐利亚绘画陈列馆新馆进行学术交流之际,我曾问过讲解人员两所博物馆中数量庞大的“印象派”收藏从何而来?得到的反馈是:得益于时任馆长契尤德个人对“印象派”的痴迷,柏林老国家画廊在他于1896年决定收购马奈的《在温室花园裡》和莫奈的《韦特伊风景》之后,成为了19世纪末最早收藏“印象派”的艺术博物馆,并于次年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收藏塞尚画作的博物馆。而当他“跳槽”去到慕尼黑巴伐利亚绘画陈列馆新馆去做馆长的时候,又在任内(1905年-1914年期间)主持收购了共计75件“印象派”及“后印象派”的作品,其中包括44件油画,9件雕塑和22件手稿,直接奠定了今天慕尼黑巴伐利亚绘画陈列馆新馆中印象派藏品的丰厚基础。他的壮举被后世誉为“契尤德的贡献”。
说到这儿,问题来了:身为一位生于奥地利的瑞士籍馆长,契尤德是如何对当时有着巨大争议的“印象派”绘画产生兴趣,并果断地把它们“收编”进他每一个担任馆长的博物馆馆藏当中的呢?答案,是被誉为法国“印象派之父”,曾拥有上万幅印象派画作,曾经经手卖掉千幅莫奈作品的丢朗·吕厄先生。
馆长契尤德对“印象派”的狂热,源自于他的一次巴黎行。在那次旅行当中,他结识了丢朗·吕厄,相谈甚欢之余,进而了解了“印象派”绘画。因此,从他手中拿到最优质的作品并被世界级博物馆所收藏,这一切都显得颇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尽管在当时,契尤德馆长在大批收购“印象派”作品时也曾饱受质疑,但他顶住了舆论压力,果断出手从丢朗·吕厄手中拿下了这些“印象派”大师作品。现如今,德国三大博物馆群引以为傲的绘画馆藏,“印象派”的作品占了极大的比重。他的果断决策,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过明智了。
除了法国印象派之外,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陈列馆新馆还坐拥极其优秀的浪漫主义画派,写实主义画派和奥地利分离画派等欧洲19世纪各阶段重要作品。包括英国“最伟大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德国浪漫主义旗帜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重要作品《晨雾中瑞森格博兰德风光》和《雪中的冷杉》以及一整面墙的德国素描大师门采尔作品,匈牙利最伟大画家米哈伊·蒙卡奇的《探望产后母子》,奥地利分离画派奠基人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玛格丽特·维特根斯坦夫人肖像》和《音乐I》等大师名作都能在不经意间掠过,甚至还包括一个摆满罗丹雕塑的展厅。
值得一提的是,四年前我在馆际交流培训时曾问过管理人员,得到的答案是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新馆所收藏的这幅透纳海景是全德国唯一一幅透纳真迹。当然,如果你想过足透纳瘾,可以前往伦敦去泰特英国馆和国家画廊,因为这俩地儿基本囊括了近90%的透纳作品。也正因如此,能够在英国境外的任何一处看到透纳的作品,都应该感觉到心满意足。
当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同时享受艺术和生活的方式时,并能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习惯,你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丰富多彩。所以,你到博物馆除了看藏品之外,也要试着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享受生活,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陈列馆老馆和新馆的部分经典藏品。当然了,你想感受更多,你必须要飞到慕尼黑,留出个几天时间,慢慢的在博物馆内享受里面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经典名作!
慕尼黑有三宝,啤酒,足球,博物馆好

慕尼黑有三宝,啤酒,足球,博物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