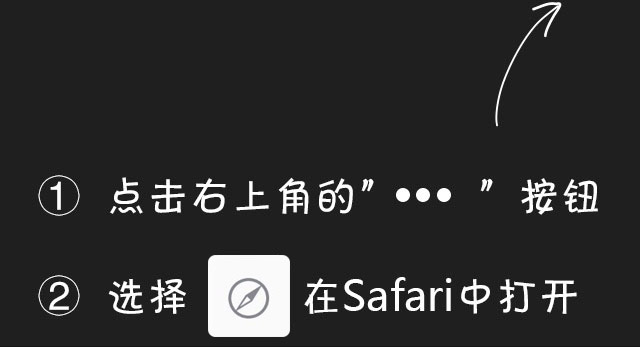我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电影或者银幕是社会的窗户。
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巴赞,他是电影银幕是窗户的一个重要的提出者,他曾经这样说过,“银幕的边框对人的行动的遮挡就像窗户对行动的遮挡一样。我们虽然看不到银幕外的空间,但我们对银幕内空间的理解其实是以银幕外空间的存在为潜在前提的,而且因为影像总是要动的,我们总是从一个空间移向另一个空间,总是想象或渴求着下一个镜头的出现。”
巴赞非常精辟地把银幕比喻成窗户,这就是从观众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为什么银幕对我们观众有吸引力。我们看银幕就像看窗户,就像想看到窗户里面的人和事,它不断吸引我们看下一步,一步一步,我们就一步一步地跟着电影镜头走,所以银幕就是具有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很像窗户的一种心理功能,我们恰好通过这个窗户看他人,观察社会,看大千世界,认识已知的或者了解未知的,甚至进入到别人的梦幻世界。
电影是窗户,它实际上是表达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说,通过这个窗户,能够满足观众的窥视心理、窥视心理也许不那么高尚,但是其实是人人都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电影,其实就是通过一种契约关系,让不合法的,平常里不能窥视的这样一种心理,在银幕上得到释放,就是导演替你窥视到了,别人的一些什么动作,那你也愿跟导演之间有一个契约关系,有一个商品的购买和被服务的关系,你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坐在那里看别人了。
所以电影史上的很多电影跟窥视有关系,包括像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情诫》,还有英国电影《偷窥者汤姆》,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马小军拿着高倍望远镜,看看别人,或躲在床底下看主人回来,这都是一些电影对于窥视心理的一种满足。电影是通过一扇后窗去看别人,这样一种隐喻性的表达。
第二个方面是说,关于电影是窗户、银幕是窗户,它其实是对电影的认识功能的一种强调。像我们所说的,经常提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像《偷自行车的人》这样一些电影,这类电影是对二战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的非常真实的一种再现,所以我们通过,《偷自行车的人》,《温培尔托·德》、《罗马十一点》这样一些电影,我们就能够看到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
比如说再通过这个伊朗新电影《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样的一些伊朗新电影,我们能看到伊朗的社会风俗、宗教,这样一些情景。还有我们经常说的,贾樟柯的电影,从他的《小武》开始,到《三峡好人》,到《天注定》,一路下来,他的电影就说带有一种平民史诗性,他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甚至是像小武这样,以前在中国银幕形象当中非常少见的,带着眼镜的小偷的这样的形象。
这一类电影,它是通过小人物,折射或者反映了大变动时期的中国底层社会现实。具有一种史诗性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乐意于把贾樟柯看成一种书记官,法国当年恩格斯称巴尔扎克是法国历史的书记官,其实就是说这一类。像贾樟柯的这一类纪实风格的电影,它也记载了中国当下的这种社会变动,像《三峡好人》啊这样的一些电影,具有一种独特的认识社会的功能。所以贾樟柯的这一类的纪实风格的电影,它的主要功能不是梦幻的功能,而是一种窗户的功能、纪实的功能、认识的功能。
人类的“偷窥欲”是如何被满足的?

人类的“偷窥欲”是如何被满足的?